讲座纪要|景海峰:“口耳相传”与“著之竹帛”【2024兴正德人文系列讲座·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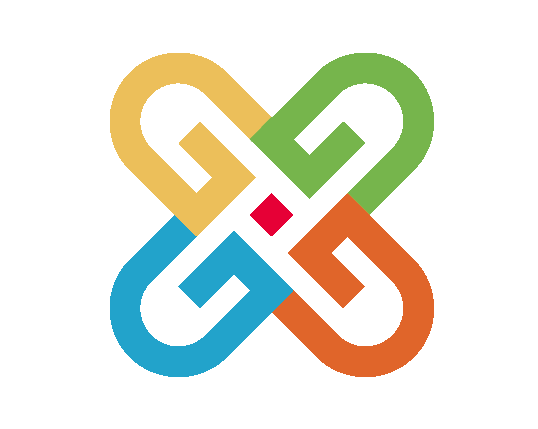
2024年3月30日下午,2024兴正德人文系列讲座首讲在深圳大学国学院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口耳相传”与“著之竹帛”》,深圳大学国学院、哲学系教授景海峰主讲。


讲座伊始,景海峰教授指出,今天所能见到的先秦经典无一例外都经历了由口耳相传向文字书写转换的过程,该过程为文、史、哲学科学者共同关注,但不同学科学者的思考角度或有不同。本场讲座即是从哲学、经典诠释的视角关照这一转换过程。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经过人们不断地认识、理解和解释,加厚了其中所负载的意义,使之成为每一个文明共同体或文化形态所不可或离的重要文本。文字是对人类早期各种记忆与思想加以继承的主要形式,而在文字书写和文本形成之前,则存在着以口头表达为中心的漫长历史时段。言语和文字作为两种传承思想的方式分别蕴含有其深刻的意义和理趣,从口语到文字记录、从简单的刻画到复杂的书写体系、从早期的刻写传抄到后世定本的流行,其间的意义铺陈、言语转换以及形态变化非常复杂,与言语和文字相对应的两种解释方式在不同文明形态中也有其独特的历史。但是大致上,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存在着这两种经典传承方式和其间相转换的过程。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景老师围绕着经典的口传形态进行了考察,指出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在成编过程中皆曾用口头的方式转相传递。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所说,三代至孔孟之前的这一阶段经典皆“相传以口耳”,战国间学者才“述旧闻而著于竹帛”,其间虽存在着著述者的“好尚”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变形走样与意义流失,但大致上先前思想的遗存能够通过所述而得以记录。为便于记诵和传播,口语或简单刻写也要适应口耳相传的要求,在刻著时采用简省和无歧义的方式增加其传递的力量与确定性,以克服“转相告语,必有愆误”的问题。
经典逐渐衍为文辞、著之竹帛的阶段中,口传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传承方式:《诗》因讽诵相传而得全于秦火;《书》由伏生口授晁错而得以存世;《礼》传自高堂生,大、小戴之前其传承亦靠口授;《易》从商瞿至田何、杨何皆为口传;《春秋》的《公羊》《毂梁》两传皆由口授传至西汉。书写材料不易获得,刻著过程又颇为复杂,形诸文字即便在汉代也并非经典传承的普遍状态。与书写形式相比,口语除具有外在条件的简易、方便和不受过多约束的优势外,在传通和理解的内在性上也因其即在性和无间距感使得书写形式望尘莫及。景老师将口语处境化特点的构成“附件”概括为四项:1、场景,随着空间的大小有所改变,从装置、器物、摆件到色彩、声音、气味、构成了场景的具体性、丰富性和生动状况;2、姿态、动作和各种身体语言,从中透显出讲者的状态、情绪、礼仪、教养,对听者的接受构成细微影响;3、表情、神态和各种面部的微小动作,与讲者所要表达的意味相结合,予听者以暗示并留下深刻印象;4、语气、强调和细微的口吻,与口语表达的内容相互纠缠,关系最为密切。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说:“语音就是灵魂中的感受的符号,而文字则是语音的符号。”语音作为对灵魂、心灵最为直接的表达,较诸文字,其在意义传达方面具有无间隔性的特点,而听者亦能直接领悟语音表达的含义。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倾听的有限性是诠释学现象的基础。”倾听是主动进入一种特定情境,在听与说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其间说者具有主导性,听者则处于从属地位。中国传统中强调的教育、教导与教化往往即采取口授的方式,在对话中呈现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等情景。宗教的布道、宣教、口谕也是如此,说与听间形成了不可逆的上下位等级关系,表现出倾听的隶属性和服从性。根据伽达默尔的看法,倾听时“流传物的真理与直接向感官显现的当下是一样的。”倾听者将这些流传物纳入自身道德言语世界关系当中,从而构成新的认识。
言语的发出者具有上位优势,对倾听者具有威权。口语话语的权力是从原初性或本体的意义上予以认定的,听对于说的依附性也只有在本源意义上才能成立。海德格尔指出:“话语本身包含有一种生存论的可能性——听。”听必须是与说相呼应、相一致的活动,才能一起构成话语的完整形态,二者具有相互激发的意味。在听与说的结构中,口语作为一种力量激活沉寂的对象,将可能蕴藏的意义不断唤起。
声音、口语是意义产生的初原,是外在化书写形制的本根,相当于四因说中的动力因。而即在性和现场感则是声音、口语的灵魂。如果即在性和现场感消失,其所传递的意义便需要借助韵读的方式还原。当其转换成文字、书写时,语音问题成为音、形、义三者的混合体,便很难从语言文字表达的整体性中将声音、口语存有的意义剥离出来。

讲座的第二部分中,景老师围绕着经典的文字与书写展开介绍和说明。景老师指出,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是中国古代经典的传衍史上的巨大变革。由口传向书写缓慢过渡的历史即是创造经典的过程。相较于口耳相传的漫长历史,只能将书写形态视作一个短程,且并非是对口语形式的取代,而只是对其的“变异”和切入。口耳相传与著之竹帛的交互性和叠加性也延时甚久,对中华文明而言,大概在两汉之交二者的主导地位才发生了转换。且口语对于理解经典的辅助意义从未消失。
较诸口语,文字因有其固定形制而不易消失、便于流传,在其系统化后逐渐成为人们记载历史、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脱离了原始语境中表达和传告的情感因素,不同于口语具有即在性及同灵魂直接的关联性,文本并不被理解为“生命的表达”。伽达默尔认为“文字性乃是语言的抽象理想性。”即是说语言转换为文字之后附着于另外的完满场域,从而构成了我们追寻另外意义的源头。文字脱开口语的直接性,同即刻的情绪、现场感相剥离,一方面失去了其“活的”情状,但另一方面又开辟了另一种当下性。也因其去情景化的缘故,为后续的理解带来了更多复杂性、可能性与歧义性,亦可说是开启了无限的释义空间。由于阅读者自我的带入,面对文本的每一次理解都可能是一次全新的境遇。阅读者应当超离出文本的规定性与有限性,读出作者“力透纸背”之处,将自我转化成一个意义之源。不同于听者无法摆脱从属性和依附性,读者在叩问文本的过程中同文本形成新的交谈场域,其理解获得了完全独立的意义。与对于文本语言学的理解不同,诠释学关心怎样来理解,理解得更好。

在中国,今文经皆是由口授转录为文字,其同口传的历史背景关系密切。古文经则多出自山岩屋壁,作为早已转写为文字的经籍,与口头语言已经有了一段距离。这两类文献的汇聚在两汉之交大体完成,经典之由口传的主导性转移到了书写物之上,思想的交流与传播亦不再依赖于特定的场景,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性和人物的处境化都产生了一种抽离化的效果。在分析口头传递向文字媒介的过渡过程时,利科指出文字是向话语打开了原始的资源,文字使话语得以独立于言说者的意图、初始听众的接收以及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作摆脱了面对面对话的限制而成为话语生成文本的条件。”
书写和阅读的关系不再呈现出听和说那样的结构,文本为人的理解活动的自由展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新的理解缘于人之精神活动的创造性,理解活动成为无所拘束的精神探险。伽达默尔认为,文字在这一意义上所体现出的即是一种“精神理解性”,文字所表达的意义需要在阅读中不断地体味和还原,而这一过程即是理解的过程,其中浸润的深入程度与想象的画面感是否清晰,决定了还原工作的成效与理解是否到位。使得文字的语义得以唤醒,在精神性的理解中重新实现了复杂的交融状态。文字是我们把捉和理解意义的桥梁,是故阅读文本不仅理解和解释了文字的蕴含,而同时也从处境的可见性和意义的投射中照见了我们自己,通过文字的“精神理解性”得以打开另一个世界。这重意义的呈现是对人自身生存境遇之本体意义的展示,而不仅仅是对语言对象物的说明。

景老师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对文本的复杂性进行了说明。景老师指出语言文字本身有很多值得理解和辨析的内容,文本的形成极为复杂,文本的形制也经历过繁复的变化。利科认为文本相对于口头语言的解放,引起的是一种真正的动荡。听与说的场景中所能表达的复杂性较为有限,文本的对象则非常复杂。古典文化的视角和眼界主要面对口语转换之后初级文本的理解和解释,现代文化则要把文本上升至同人存在的本体意义同步理解的关系,是故产生出各类复杂思想。文字把人的认知活动和已知对象做出分离,使人的内省意识日渐增强,打开了心灵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通过书写方式将历史经验和口头记忆做了进一步的筛选和深化,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思想范式和基准性的元概念。阅读使得信息传递的层面得以扩大,超离了“在场”的有限性和束缚性,认知活动就进入了一个反复循环、交互激发的状态,思想创造的活力和普遍性都大为加强。人有意识的活动与合目的性的成就在对被记录的文字进行整理、编排的过程中得以明晰化,进而形成了社会历史的共识性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一个文本的成型过程便需要话语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不断地相互“试探”,以造就一个可以进行公共理解活动的场域。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样一种清晰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进入历史的过程。
就物质条件而言,记录文字所适合的材料的特殊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文本的记载方式。汉唐时期文本制作不易,不便流行。宋代随着纸品的普及和印刷术的提升,刻书印本逐渐取代写录、传抄,刊刻书籍为阅读的便利提供了更大可能,即为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场域,也为经典文本的精细校勘、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最早的书写体式来看,经典材料的集结、汇编和成型,与文章的出现处在一个长相伴随的过程,二者间关系紧密。照此思路理解,中国古代文体即起自五经。文章体式的演变是经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视角,研究文章体式亦必须了解经学发展的历史。如果从经典之间的关系或形成过程中相互影响,以及内容上的交融、重叠和穿插等情况来看,文本形态就更显复杂。譬如《春秋》从形成期开始就伴随着解释活动,《公羊传》《榖梁传》《左传》皆系经传合一的形态,其成型即是解释的产物,《春秋》本经的独立意义反而消失。
讲座最后,景老师指出,从口传到记录成文,再演变成为有系统体式的各类文章,为书写与阅读的诠释学间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汇聚成篇的经典成为观念交互性展开的集散地,亦成为人们不断理解、建构自身文明历史,并进而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进入与理解的思想源泉。通过对文本的对比、仿照和交流,能够借以确证我们当下认识与选择的合理性,并从时间的流变状态中,体味和捕捉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不同于口语传递具有即在性和瞬间性,对文本的思考与理解不需要通过不完整的片段记忆来还原话语的意义,而是可以无限期的涵泳其间。经过反复查证、对照与检视,以进入到文字所欲表达或转达的意境之中。此种理解已远远超越了原初的情景,并且需要在前人理解的遗存物中迂回跋涉,排除错谬。每一种对于经典文本的理解,同时也就是对于前人之理解的理解。在这一意义上,经典必然和解释相联系,没有解释便没有经典,经典的历史亦即是诠释的历史,对经典的注解便成为各大文明的显著标志,也是其延续传统、传承文化和创造观念的一种基本方式。



提问环节中,讲座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向景老师踊跃发问。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王顺然就以下三个方面对景老师进行提问:其一,经典由口传固定化为文字是一个有目的性的选择过程,而选择的标准更像是经典形成的原则,那么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文字固定下来之后,强化了解释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经典的解释过程中,带有稳定性的文字何以能够带来诠释的复杂性;现代社会中新的媒介载体超越于语言文字,使得理解经典的过程更加生动,这种形式应当如何在经典展开和理解的脉络中进行更进一步运用?现场同学还就如何理解经典本义与诠释学意涵、文字是否同口头语言一样具有权威和力量、如何看待经由考据已经证伪的经典文献等方面进行提问。景老师对老师和同学们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后,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主讲人简介

景海峰,深圳大学国学院、哲学系教授,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曾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大学等校做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儒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著有《熊十力》《梁漱溟评传》《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诠释学与儒家思想》《经典诠释与当代中国哲学》等,另有编著十余种及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兴正德人文系列讲座”项目启动于2018年1月,旨在推动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的发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兴正德人文系列讲座”内容涵盖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专业领域,由国内学界资深教授和知名青年学者担任主讲人,面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自项目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讲座59场。






